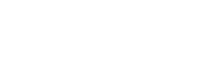基因编辑工具提供了预防疾病的新方法

玛雅szatai的插图
Adele Ricciardi通过练轻松导航猎人建筑的走廊和楼梯。在其实验室和教室度过六年后,医学院已经感觉像家一样。
“当我来到医学院时,我想找出翻译的研究,弥合基础科学与医学之间的差距,”Ricciardi说。毫无疑问,她在医学院找到了它。Ricciardi在三个不同的实验室中花费了她的日子,弥合差距和跨校园的转化研究 - 以及追求她的M.D./PH.D。程度。
Ricciardi的工作必须多方面。在医学研究的景观中,特别是在医学院,特别是传统上不同的领域的交配产生多产的收获。Ricciardi的家庭基础实验室之间的协作研究已经生产了一种比众多赞扬的CRAP / CAS9更精确的基因编辑工具,开发了一种纳米镜,并确定它可能减轻的遗传疾病。Triple Helix的工具是在Peter M. Glazer,M.D.'87,Ph.D的实验室中开发的。'87,HS'91,FW '91,椅子和罗伯特E.猎人治疗放射学教授,以及遗传学教授。三重螺旋是近十年的合作的果实。
2009年,Joanna Chin,M.D.'10,Ph.D.'10,在一年一度的M.D./Ph.d提出了对Triple Helix的研究。撤退。DNA编辑工具很有希望,但安全地将其渡过细胞,证明了一个看似难以应变的挑战。偶然,附近的妮可阿里麦克妮海报,M.D.'14,Ph.D.'14,说明了纳米颗粒的开发,其可以将复杂的分子与细胞心脏递送。每个人都很快意识到另一个项目在她自己的问题上解决了一个问题:下巴有一个没有送货车的编辑工具,而McNeer的纳米颗粒是有效载荷的渡轮。
“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完美的协同作用,”格拉泽说,谁是下巴的主要调查员。在下巴和麦克妮的午休会议以来,协同作用扩大以生产众多论文并涉及更多的研究人员。“这是一项大幅富有成效的合作,”博士·萨尔茨曼,博士,生物医学工程和化学工程基金会教授,以及麦克奈的主要调查员的细胞和分子生理学教授。
eliasquijano,一个m.d./ph.d。学生,也适用于Glazer和Saltzman的实验室。最初是耶鲁学院的英语专业,经过萨尔茨曼,Quijano成为一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,后来Saltzman的实验室经理。他现在参与了三重螺旋研究,但他作为本科的课程引发了他对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的兴趣。
“这真的来自看着科学如何进入临床医学的第一个例子,”他说,“以及如何临床需求可以推动科学过程本身。我认为看到相互作用 - 看到科学与医学之间的舞蹈 - 是真正吸引了我的领域的东西。“
像Quijano一样,Ricciardi在Saltzman和Glazer的实验室中致力于基础科学,精炼纳米粒子和他们提供的遗传有效载荷。她在助理手术教授(儿科)助理教授David H. Stitelman,M.D.的实验室里获得了她的临床修复。“我对工程有兴趣,”Ricciardi说,“因为我认为它与医学很好。”联盟意味着她可以“以非常人性的方式应用科学” -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,它给了她鹅肿块。在这个阶段,应用科学正在用小鼠模型运行,但人类的影响是可触及的。
“如果你能基本上治愈疾病,或消除患有疾病的症状,非常少数偏离目标效果 - 我认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未满足需要,”Ricciardi说。
三重螺旋行动
Ricciardi沿着最终走廊走下去,拉出她的身份证来解锁Glazer Lab。在迎接实验室队友之后和咨询几个Hefty实验室笔记本之一,检查其即将到来的实验中的DNA浓度,Ricciardi在目前的研究主题上推动:F8 571。在凝固到外壳的外部观察者中,匆匆的生物是一种表面上平均鼠标。然而,在分子水平上,某些东西是危险的:小鼠DNA代码中的单点突变,用于罕见但有害的血液疾病,地中海贫血。该病症的特征在于弱,快速到期的红细胞和导致贫血。Tantalizing的微小遗传误差及其外渗后果是推动重写代码的努力 - 不仅适用于这种鼠标或这种疾病,而且对于人类患者的囊性纤维化和镰状细胞贫血病症。
遗传修正以DNA类似物(肽核酸或PNA)开始。在纳米颗粒中被包封,PNA增加了对细胞的“DNA - 以及引起疾病的突变。由其序列引导,这将在DNA中寻找与其匹配的匹配,在错误的DNA片段和周围围绕错误的DNA,轻轻地脱落并取代其合作伙伴股线。与DNA两侧的结合,这一新灯丝扭曲了经典的梯子样螺旋,形成临时三螺旋:PNA-DNA-PNA。这种异常布置在细胞机器中掀起了警告响铃。Glazer说,扰动细胞在其遗传构成中感应了遗传构成的膨胀凸起 - 就像你的鞋子里那样。显着的布置使细胞的修复机制产生,其加速将原始供体DNA(也被纳米颗粒递送)滑入受损基因,修复初始突变。
三重螺旋已被用来校正鼠标模型中的原因导致突变。“我们治愈了贫血小鼠,”Glazer说。“我们做了四种纳米颗粒注射,而30天后,它们被治愈。”该技术比常见的基因编辑CRISPR / CAS9修复约5%的靶细胞,而CRISPR将以30%至50%起作用。然而,偏离目标效果(在基因组中的其他地方在其他地方创造不需要的突变)在三重螺旋中也比CRISPR-10,000至100,000倍下降得多。“我认为人们会改善克里普尔克核酸酶,使其略微滥交 - 但我们已经在那里,”Glazer说。“我认为我们的偏离目标效果少于CRISPR将能够进入。”Glazer期望三联螺旋在两年内进行临床试验。
“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阶段,我们在PCNA设计和药物交付融合方面有进步,”Quijano说。“我们到达两种技术准备好临床翻译的地方。”
杜斯拔湾的未来?
对于许多人来说,人类基因编辑的前景提高了一种缺陷症的令人不安的污染般的幽灵,其中精英创造了具有增强的精神或身体敏捷性的定制儿童 - 甚至纯粹的审美特性,例如特定的眼睛或毛发。
“我对我的高中生物课具有非常鲜明的回忆,他们在电视上转过电视并观看Gattaca,”Ricciardi说。1997年的电影主演Ethan Hawke描绘了一个未来的世界,遗传工程的儿童Excel,而自然的是持续偏见。来自Glazer和Saltzman Labs的作品具有更具良性的目标。“我们并不试图引入有利的特性,例如改善的智力或运动能力或音乐实力。我们想要做的是消除儿童疾病的负担,“Ricciardi说。“有遗传障碍的孩子们将在其余的生活中致力于医生的任命。他们将采取慢性昂贵的疗法来帮助改善疾病的症状。如果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来减少患者,家庭和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 - 这就是我们治疗的目标是什么。“
“它的最令人兴奋的方面是看到这些分子如何临床应用,并且看到治疗人类疾病的可能性,”Quijano说。
Saltzman自他的研究生课时以来一直在追求跨学科研究,研究化学工程,然后医疗工程成为生物医学工程师。他说,沉浸在两个工程和医学世界中,为成为一个合作科学家铺平了道路。“这么大的是了解文化,了解人们使用的语言,”他说。
“许多方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问题更加困难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涉及人们的合作团队 - 经常有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的人,“Saltzman说。所谓的简单问题有他们的问题和答案在同一个学科,而艰难问题来自多个字段。“Peter [Glazer]和我的科学学科,我的科学学科非常重叠,而且作为一支球队,我们可以取得进展的问题,萨尔茨曼说。
Glazer和Saltzman的合作一直是生产论文,专利和伙伴关系 - 现在正在成为原型的。奥莱斯,萨尔茨曼说,是“一个庞大的大学 - 智力 - 而是一个漂亮的大学,社区真正有价值。这足够大,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人 - 所有不同的专业知识 - 但它足够小,因为它们并不是很难找到的。“多学科环境可能是矛盾的,在那里,这些研究人员是Quijano,Ricciardi,Saltzman和Glazer正在寻找他们的利基。
“萨尔茨曼说:”这对我来说很重要,“这是一个与人合作。”“如果我没有,我就不竞争。”